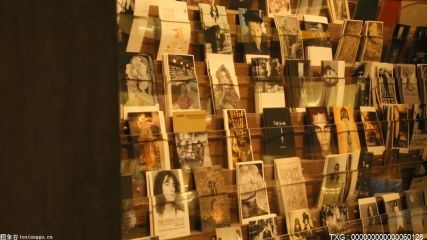“吏者,民之本纲者也,故圣人治吏不治民。”
古往今来,吏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点,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与存亡,因此如何进行吏治管理成为统治阶级从未间断的探索,秦汉王朝也是如此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秦时若要成为官府吏员,必须经历“学吏”的过程。秦学吏之风的盛行,大致可追溯到商鞅时期。
商鞅变法时提出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,又言:“置主法之吏,以为天下师。由此,秦国制定出重法令、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。韩非发展商法思想,明确提出“民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”的观点,得到秦始皇的赞同。公元前213年,李斯向秦始皇建议:“若欲有学法令,以吏为师。”此建议得到皇帝批准。
至此,秦“以吏为师”的学吏制度正式得到推行,以法为教在秦国盛行。学吏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更是得到迅速发展。除了统一思想的考量外,很大的原因在于大一统国家的行政事务、百姓纠纷以及经济往来等事务数量剧增,而熟悉秦制的吏员数量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政务需求。学吏制度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。
在该制度下,学习诸种为吏技能的人,统称为学童。学童经过学习,考核合格后方可被正式任命为正式的吏员。学童的出身秦代的学童专指学习文字书写、文书工作处理的人。他们在取得合格的成绩后,一般会成为各级官府中的文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:汉兴,萧何草律,亦著其法曰:“太史试学童,能讽书九千字以上,乃得为史。
又以六体试之,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,字或不正,辄举劾。”
又《说文解字·叙》载:尉律:学童十七巳上,始试。讽籀书九千字,乃得为史。又以八体试之。郡移,太史并课,最者以为尚书史。书或不正,辄举劾之。
从材料可知,汉代学童主要学习文字书写,根据学习的程度不同,可以担任一般的“史”职,乃至尚书、御史的文吏等工作。秦时学童的相关史料流传至今的相对较少,以往的研究中,通常以汉时学童情况推测秦朝学童状况,张春龙的《里耶秦简中迁陵县学官和相关记录》一文公布了一些简文,其中保存了秦时“学童”的直接史料:简14—18正面:廿六年七月庚辰朔乙未,迁陵拔谓学佴:学童拾有鞫,与狱史畸徼执,其亡,不得。上奔牒而定名事里。
它坐亡年月日,论云何,[何]辜,故或覆问之,毋有。与狱史畸以律封守上牒。以书言。勿留。反面:七月乙未牢臣分韱以来亭手。畸手。15—172正面:廿六年七月庚辰朔乙未,学佴亭敢言之:令曰童拾史畸执定言。
今问之毋学童拾。敢言之。反面:即令守行简文中提到“学童拾”,“拾”是人名,“学童”就是“拾”的身份,类似“狱史”是“畸”的身份一样。这直接证实了秦时“学童”的存在。学童依据其出身不同,又有“史子”和“弟子”的分别。“史子”顾名思义即史之子,也就是从事文书工作的吏员之子。这些人继承父业,依旧从事文书工作。
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指出:“古时以文书为职务的史每每世代相传,要从小受读写文字的教育。“史子”是众多学童中特殊的群体,他们由于家庭背景影响,秉承家学,耳濡目染,更容易掌握史之职,故而受到特殊培养。“史子”的存在,表明秦的官吏选拔方式中,有世官制的遗存,在出土的《睡虎地云梦秦简》中,有凭借父亲或者兄长的职位而获得官职的规定。
称之为葆子制度,官吏子弟可纳入“弟子籍”,享受一定特权,这里不做多述。
“弟子”则是指投靠在某官吏门下的弟子。这些人多为民间子弟。他们通过学习文字书写以及秦国法律,同样可以成为吏员。晋文明确指出秦代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奔某官吏门下做“弟子”。“弟子”虽然不是正式的吏员,但已经可以享有一定的特权。《睡虎地秦简》载:当除弟子籍不得,置任不审,皆耐为侯(候)。使其弟子赢律,及治(笞)之,赀一甲;决革,二甲。
由此可见,弟子有专门的名籍,即“弟子籍”。其中“当除弟子籍不得……皆耐为侯(候)。”
表明只要符合条件,都可以申请“弟子籍”。在学童为弟子期间,根据法律规定官员役使弟子,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。
而且不能随意笞打,否则会受到罚一甲的惩处,如果情节严重,惩罚加重。
可知“弟子”相对于普通人,是享有一定特权的。
二、学童的培养在以吏为师的制度下,学童多跟从吏员,一边学习,一边也帮忙处理一些事务。岳麓秦简载:学书吏所未盈十五岁者不为舍人。这里“学书吏所”的人就是学吏制下的学童,而“吏所”就是学童学习的地方。“吏所”即官吏办公所在的地方。
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——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》报道了编号为J11—J112的标本。
赵瑞民指出:“该组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在背面都有一条相同内容的公文。一件公文抄写12份,这是很特异的现象。赵瑞民联想甲骨文里出现的习刻,推测这些重复的公文应该是为了学习、练习所用,进而指出“这种学习是在官府办公场所进行,因为公文不会流出官府之外。李兵飞在《出土文献所见学童、弟子与舍人研究》一文中以秦官吏处理日常政务的工作量进行推测,认为秦官吏日常工作量之大,还要指导弟子学习。
很有可能是在官府而非家中,在官府可以让弟子切身的学习与帮忙服务,这是一举两得之事。
除了跟随吏师在工作过程中学习,秦还有专门的教学场所。岳麓秦简留存一条材料:史子未傅,先觉(学)觉(学)室。又睡虎地秦简《内史杂》记载:非史子殹(也),勿敢学学室。这里提及的“学室”,即秦时官方的一种学校,是“史子”的学习场所,“史子”不必像一般弟子,混杂吏师工作场所半工半读。有关学吏者学习的内容,最基本的是文字书写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:汉兴,萧何草律,亦著其法曰:“太史试学童,能讽书九千字以上,乃得为史。
又以六体试之,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。吏民上书,字或不正,辄举劾。
由此可以看出,汉代学童能否取得为吏的资格,能书写的字数以及字体是重要的标准。汉承秦制,秦代当与此相差不远。近年来,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习字简,这是当时学吏者练习书写的直接证明。
史料中也有秦代字书的记载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《苍颉》七章者,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
《爰历》六章者,车府令赵高所作也;《博学》七章者,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;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,而篆体复颇异,所谓秦篆者也。是时始造隶书矣,起于官狱多事,苟趋省易,施之于徒隶也。汉兴,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,断六十字以为一章,凡五十五章,并为《苍颉篇》。材料中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皆为秦人所作,其上承《史籀篇》,下开《仓颉篇》。
《史籀篇》、《仓颉篇》分别以大篆、隶书书写,是周代、汉代学字的教科书。
同理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则应系秦代学童学习文字的课本。其内容今已不可考,幸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保留了《急就篇》中部分文字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《急就篇》“皆《苍颉》中正字也。这里《仓颉》为汉代《仓颉篇》,上引材料可知《仓颉篇》总结自秦三部字书。
由此我们得以通过《急救篇》内容,窥视秦字书相关内容。
三、学童的转正学童经过严格的培训,要通过考试的方式取得为吏的资格。岳麓秦简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:中县史学童今岁会试者凡八百卌一人,其不入史者一十一人。臣闻其不入者,泰抵恶为吏,而与其典试以为潦东县官佐四岁,日备免之。日未备而有迁皋,因处之潦东,而皆令其父母妻子与同居数者从之,以罚其为诈,便。
臣玫斯请。制曰:可。廿九年四月甲戍到胡阳·史学童诈不入试令·出廷丙廿七。从材料可知,中县一年参与考试的学童有831人,对于一个县来说,这种比例是不小的。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当时学吏者的身份并非仅仅是“史子”这种家学传承者,也包括大量的民间子弟。而其中“不入史者一十一人”,可见考核是有淘汰率的。
但这种淘汰率,显然不高,这与当时亟需大量吏员的背景有关。通过考试成为正式吏员。
是学吏者的权利,同时也是义务,尤其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,所以当时法令明确对“史学童诈不入试令”者要有惩罚。这与“驾驺除四岁,不能驾御,赀教者一盾;免,赏(偿)四岁(徭)戍”的法令相互印证,即国家付出努力培养,如果不合格,或者逃避考试,必然要受到惩罚,补偿国家损失。从“驾驺除四岁,不能驾御,赀教者一盾”的规定来看,教学者也会受到连带责任,一并惩罚。
经过考试合格者,学童取得为吏的资格。但对于吏员的任用是有要求的,关于秦代任用吏员的规定,新出土的岳麓简有部分记载。
置吏律曰:县除小佐毋(无)秩者,各除其县中,皆择除不更以下到士五(伍)史者为佐,不足,益除君子子、大夫子、小爵及公卒、士五(伍)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。
其新黔首勿强,年过六十者勿以为佐。人属弟、人复子欲为佐史。
这则简文记载了县级官府任用吏员的规定。其中优先任用为佐的人选是“不更以下到士五(伍)史者”,这些人显然是经过考核之后,从学吏者到拥有为吏资格的人。如果这些人不够,会从君子子、大夫子、小爵及公卒、士五(伍)子年十八岁以上的备员中选择。这些“备员”很可能就是未经考核而进入“弟子籍”的人。
他们或有家族从政背景,或正在学习这些技能,故而在人口不足的时候可以提前补充进入吏员的队伍。
结语官吏在治国兴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”吏治问题并非与人类共生共存,而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产物,要缓解官吏内部矛盾,需要指导思想和制度建设双方面的协调与配合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对各级官吏的管理严格按照秦官吏考核之标准执行,在严格的官吏管理制度下,各级官吏兢兢业业,认真施政。
汉初,统治阶级在吸收秦朝官吏管理制度中的合理成分,剔除官吏管理制度糟粕,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。
实行以黄老思想为吏治指导思想,皇帝和各级官吏严格遵循黄老治吏的方针,发展到景帝时期,西汉社会活力已经恢复。
国库充盈,社会稳定,百姓安居乐业。武帝、宣帝时期,采用“王霸道杂用之”的吏治观,对官吏恩威并施,内儒外法,成效斐然。简单来讲,秦到武、宣时期的统治阶级对官吏的管理经历了崇法——重黄老——外儒内法的探索。
秦朝崇尚以法治吏,在统一之前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有利于迅速集结全国力量努力耕战,取得战争胜利。但另一方面,统一后的秦朝仍然秉持严以治吏的政治理念,君臣离心,二世而亡。
这是秦不合时宜的推行战国商法、忽略统一后政治环境之不同、忽略各级官吏价值取向等因素所导致的直接后果,使“朕为始皇帝,后世以计数。
二世、三世至于万世,传之无穷”成为秦始皇的一厢情愿。汉以来,从高祖至昭宣,吏治思想在短短百余年由黄老转向儒法兼用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简单的去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。
而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,不管是汉初的黄老思想为吏治指导思想,还是武帝以后的儒法并用。
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情况而做出的正确选择,二者都取得了恢复社会经济、稳定社会秩序、安抚百姓的目的。
新国用黄老,平国用儒法的吏治理念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。
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一直遵循的治吏理念,甚至对韩国、日本、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政治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